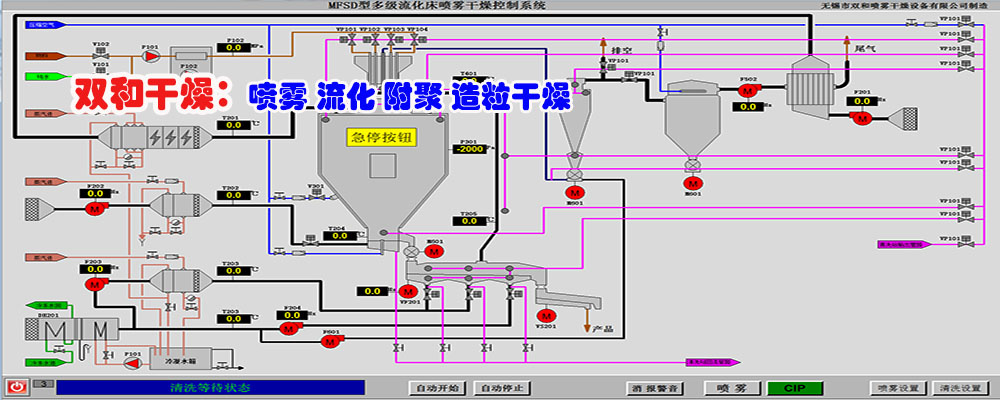

廣西興業縣大平山鎮南村,受侵害女童小雨(化名)的家。
從表面上看,廣西玉林市興業縣大平山鎮南村算不上一個貧窮、閉塞的村莊。從玉林市區出發,往西北方向一路行駛約30公里就到了:在平原中拔地而起的丘陵,“俯瞰”著村莊高矮不一的屋舍,一條緩緩流淌的溪流從村前繞過,與之相連的,就是薄霧彌漫的田野。
年近歲末,這個有著2300多口人的村莊,在冬日和煦的陽光照射下,老人們背著手慢慢踱步,婦女抱著孩子溜達串門,黃狗臥在村道上,放學后的孩子三三兩兩一路嬉戲。
就是在這個寧靜的村莊,一個留守女童,在長達兩年的時間里遭到村里多名中老年人性侵。憤怒的父親發現真相并報警后,司法介入,最終10人被判刑。讓人意想不到的是,這不是一個罪惡被制止、壞人遭懲治的故事,反而是女童及其家人遭受了村民的“敵視”,“都是她,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。”
“爺爺輩”施害者
廣西玉林市興業縣大平山鎮南村,一個留守女童,在長達兩年的時間里遭到村里多名中老年人性侵。性侵的事實,最終因法院的判決而得以確認。興業縣人民法院分三批審判:2013年10月14日判1人猥褻罪,刑期2年6個月;4天后,3人因強奸罪獲刑9年、7年、7年;11月27日,另6人一同以強奸罪獲刑。
宣判后,只有1人提起上訴。他并沒有否認與幼女間有身體接觸,但他認為自己不是主動的,而且認為量刑過重。
10人性侵的是同一個女孩小雨(化名)。她2000年3月出生,受害時還是一名小學生。施害者獲刑時,年紀最大的76歲,最小的也有44歲了。
在小雨的敘述中,強奸過她的至少有18人,其中15人是她同村的長輩——大部分是爺爺輩。在持續2年的時間里,每人平均性侵三四次。最多的一個,60歲的陳美光,法院認定達15次。
第一次性侵發生在2011年,當時小雨只有11歲,而施害者黃延來已經74歲了。那是4月份,春季放農忙假的最后一天,“瘦瘦小小的小雨,跟著奶奶去山嶺間的田里插秧,后來小雨自己一個人去撿田螺,撿著撿著,她就離奶奶越來越遠了。”
噩運在此時降臨,“正在山嶺腳下砍竹筍”的黃延來發現了孤身一人的小雨。她成了“獵物”。“強奸時,身旁放有一把砍竹筍用的那種鐵的長鉤刀。”
這些情節是家人根據小雨的回憶整理出來的,家屬試圖弄清楚罪惡是如何一步步發生的,為什么會卷入這么多人。法院的判決書則要簡單得多,只有對單一犯罪事實的認定。
法院的認定與小雨的陳述也存在出入。根據判決書,黃延來犯罪的時間是在2011年10月的一天中午。這個時間點,讓黃延來的強奸順序至少排在了72歲的周振成和60歲的陳美光之后。而小雨則堅稱,黃延來才是第一個施害者。
黃延來得逞后,開始把小雨介紹給其他人。在小雨放學的路上,黃延來嬉笑著把小雨指給別人看:“就是這個,很容易就可以讓她干那事。”
他所說的“很容易”,是指每次性侵完之后,給小雨15元或20元不等的零花錢,讓她不要聲張。按照小雨的講述,后來黃延來甚至發展到叫人到她家來強奸她。
經由黃延來的“介紹”,參與性侵的人數越來越多,就像滾雪球一樣。除了黃延來,周振成和陳美光也成了介紹人,陳美光甚至有叫來人后,兩人一起輪奸的情節。
據小雨回憶,黃延來第一次把陳美光拉來的時候,陳美光還說,“孩子這么小,快放了人家”,并未實施性侵。但是之后,陳美光也“淪陷”了,并成為強奸次數最多的人。
被拉進來的人群中,只有一個人守住了底線,未曾參與性侵。據小雨陳述,陳美光還喊過一個傻子來,但是那個傻子“連碰都不敢碰”她。
面帶憤怒的同情者
南村的村干部和南村小學的老師認為,性侵是隱秘進行的,除了涉案人員,外人難以知曉。南村小學一位李姓老師說,村民應該不知情,“如果外人知情,我想應該不會發生那么長時間了。”
李老師說,在小雨就讀的兩年時間里,小雨的“死黨”從來沒有向老師透露過半點風聲,而“小孩子的心態,是有什么情況都喜歡跟老師匯報的”。
然而,只要到村里隨便走一走,就會發現所謂“不知情”的說法,顯得有點站不住腳。
2013年12月31日下午,在離小雨家門口十多米遠的馬路上,記者采訪小雨的爺爺、奶奶以及叔公時,須發已白的叔公聲音激越地表達著自己的憤怒,原本寂靜的一角,引來了幾個村婦圍觀。在墻角,一個背著孩子的婦女靜聽了半晌,似乎是不同意這位叔公的說法,她向記者勾了一下手,然后轉身離去。
記者隨后跟著她,走出一條狹窄的巷道,已經有三四位婦女站在那里。“你是記者是吧?你千萬不要只聽他們一家人的,事情根本就不是那樣子的,”一位皮膚黝黑、年近五旬的婦女有些激動,“你不信可以到村里隨便去問一問。”
“那真相是怎樣的呢?”記者問。幾個女人相互看了一眼,有人忍不住笑出聲來,帶著不好意思講出口的羞澀表情,然后迅速用眼神“投票”,推出一位代表。
被“推出來”的婦女沉默了一下,表情嚴肅,帶著憤怒:“都是那個小女孩主動的,去到人家老人屋里,‘你有錢吧,要不要啦?’‘30塊都沒有嗎?’就這樣的,都是她,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。”
“是啊,是啊,就是這樣的,老人都是讓她給害的。”背著孩子的婦女同聲附和,用手指給記者看黃延來的住處——屋子隔著村道數米,離小雨家也不過百來米遠。76歲的黃延來是村里的五保老人,按照村支書的說法,“那些老人從來都沒有做過犯法的事情。”
這或許也是老人們被判坐牢后引起村民同情的原因之一。在記者問到“你們有沒有想過,那只是一個孩子”時,圍在邊上的村民沉默了一下,隨即有人反駁:“知道要錢,就不是孩子了。”或許覺得不妥,又補充道:“都怪老人不懂法,沒滿18歲,是吧?”
傳統又現代的村莊
南村在興業縣算得上是個中等規模的村莊,它在“現代化”建設上已經頗為可觀。靠著在廣東等地打工的收入,村子里已經興建起不少三四層的新樓,陽光照射下,新安裝的鋁合金門窗閃閃發亮。村子的道路都已修好了,東西兩側的廣場,各修了一個籃球場。自來水也通向了每家每戶。從外觀上,村民的生活在積極向城市生活靠攏。
在傳統的修復方面,南村也在積極進行。進入村口,必須要鉆過一座高聳的牌坊,那是村民集資興建的,牌坊是南村的“龍門”,代表村民精神世界一角的,是“龍門”左右兩側鐫刻的“富貴”和“榮華”。
村里曾有一座廟,在上個世紀60年代被“紅衛兵”破四舊給拆掉了,到了90年代,村民重建后,又被政府拆了。這一次,村子里到處張貼著捐款者的名單,有人出面再次集資,計劃將廟宇重建起來。
這個行走在傳統與現代邊緣的村莊,在面對女童被性侵這件事情上,似乎有著與外人不太一樣的觀念。在村民眼中,老人性侵后給了錢,也沒有遇到激烈的反抗,女童就不值得同情。
即使是小雨的父親龐玉強,也沒有清晰的權利觀念。遇到村民稱“你女兒是在賣”時,他還是會一時語塞,囁嚅一下,“他們說是賣哦,哪有30塊來賣的?”他自問自答地辯駁。
龐玉強的家在村子的最后面,緊挨著山坡,這一片就像村里的貧民區,房子老舊,還留存有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那種低矮的泥土房。
3間紅磚房,中間是堂屋,供著祖先的牌位,面前擺放著六個空的銅酒杯。堂屋的兩側各有一間十來個平米的臥室,分別擺放兩張床,黑黢黢的,凌亂不堪——這樣一棟房里,住著10口人,龐玉強一家5口、弟弟一家5口。
10米開外,就是龐玉強父母的住所,是那種破舊的泥土屋,幽暗潮濕,空間逼仄,出門就是鄰居家那一面青磚砌成的墻壁。
因為貧窮,龐玉強和弟弟都帶著老婆在廣東打工,他的孩子和弟弟的孩子一道,留在了家里給父母來照顧。但老人也有自己的麻煩,龐玉強的父親12年前出車禍,雙腿殘疾,只有拄著雙拐才能勉強走路。照顧留在家里的幾個孩子,老人明顯精力不夠。
正是這個殘疾的老人,在村子里有著緊張的人際關系。在南村,人均只有7分田,在靠地吃飯的時代,村民間因為田地糾紛而關系緊張。龐玉強說,父親確實因此與村民發生過矛盾,但“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”。
村民們說,“他們家的兩個老人好兇的,誰敢跟他們講?”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誰愿意惹麻煩?”
村莊里的“高墻”
2013年一整年,42歲的龐玉強都在為女兒的事情奔走,他希望懲治那些施害者。只是讓他沒想到的是,通過報警、網上申訴等途徑,法院最終宣判后,等待龐玉強的卻是“歧視、憤怒”等情緒筑成的一道“高墻”,將他們一家隔絕在村民之外。
這道“高墻”看似無形,卻讓龐玉強碰得“鼻青臉腫”。他所能做的,就是把女兒送到親戚家讀書、生活。而他自己,在出門時裝作沒事人一樣,從那些熟悉的“陌生人”中間快速穿過,回到家后,就躲著,一整天都不出門。
據龐玉強介紹,自從報警之后,自己在村子里就沒有了朋友,沒有人可說話。他擅長泥水活兒,原來好多人找他去幫忙,但2013年一整年呆在家里,再也沒有人上門了。“誰還理你啊?”龐玉強說。
更嚴重的是,如果小雨單獨出現在公共場合,就會面對村里的許多風言風語,說她“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別人買的”之類。
在報案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,龐玉強堅持送女兒去上學,這樣別人就不敢指指點點。村民們都知道,在發現女兒遭遇性侵的事實后,這個中年男人曾操著刀,要去砍死黃延來、周振成和陳美光等。只是家屬的勸阻,最終讓他放下了刀,選擇了法律武器。
南村村委會干部也承認村莊里確實存在著“歧視”。一位村干部告訴記者,“她(小雨)去同學家玩,都會被同學的父母從家里趕出去,不讓她進家門。”
這些隱形的傷害,龐玉強和家人只能默默承受,對這個村莊的人心,他無能為力。
在這樣的環境中,未成年女孩小雨的人生還要負重前行。似乎是為了彌補對孩子的愧疚,龐玉強決定,2014年,讓老婆一個人出去打工,他自己就留在家里看著孩子們了。



